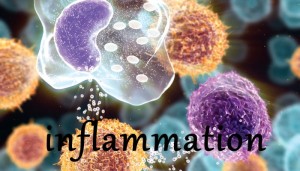供氧不息,生命不止。氧是人类的生命之源,有氧呼吸是细胞产能的基础,正所谓“人可一日不饮,一周不食,但不可一刻缺氧”。炎症,则是人体为了抵御外界环境时时刻刻都在上演的“人体保卫战”。缺氧和炎症,这两种听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在临床研究者的眼中却不可思议地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难以想象的是,与缺氧有关的物质成为了当今各种炎症反应甚至癌症的治疗新靶点。
缺氧将炎症进行到底:从高山病、器官移植、糖尿病等领域得到的启示
我们先从各种实际现象出发,看看缺氧与炎症之间是否存在传说中的不解之缘。高山病(mountain sickness)是指人体对高山缺氧环境适应能力不足而引起的一系列临床表现。科学家研究了这些缺氧人群体内的各种因子,发现与炎症相关的IL-6、IL-7、C反应蛋白都较正常有所增加。在器官移植领域,移植物的缺血缺氧会增加炎症反应、移植物失败或者排异等的危险性。例如在肾移植和肺移植领域,缺氧的移植物中toll样受体4(一种参加非特异性免疫的蛋白质)表达都有所上升。另外,在我们熟知的糖尿病研究领域也能找到缺氧促进炎症反应的证据。脂肪组织中,如果氧气供不应求,那么各种炎性的脂肪因子就会“趋之若鹜”,结果导致巨噬细胞浸润而引起慢性炎症,成为胰岛素抵抗的一大“元凶”。
炎症将缺氧进行到底:从肠子说起
我们都知道,肠腔内是厌氧环境,黏膜固有层细胞则日夜被浸泡在这种相对缺氧的环境中。研究发现,如果肠子发生了炎症,例如常见的炎症性肠病(IBD),黏膜固有层细胞就会变得更加缺氧。这种现象似乎更好解释:细胞需要更多的能量来抵御炎症,而由于栓塞、损伤、压迫等因素使得代谢底物减少,并且各种细胞内病原体会耗氧,因此细胞处于缺氧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炎症反应,缺氧的细胞并非袖手旁观,而会参与到这场保卫战之中。具体的机制就可能与下面要提到的PHD-HIF系统相关。
缺氧和炎症之间的“鹊桥”:PHD-HIF系统
在缺氧状态下,机体理所当然地会激发各种调节机制以适应缺氧,例如尽力呼吸、增加血流速度、启动应激反应等。在这些宏观的病生理过程背后,有一个转录调节因子在做着大量的“幕后工作”,这就是缺氧诱导因子(hypoxia-inducible transcription factor ,HIF)。HIF是一种DNA结合蛋白,由一个α亚基(HIF-1α或HIF-2α,前者普遍存在,后者只存在于某些组织中)和一个β亚基(HIF-1β)组成异源二聚体而成。
细胞对缺氧的适应过程依赖于HIF的参与,它只有在缺氧的时候才会被激活。而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常氧下α亚基的核心脯氨酸能被氧敏感性脯氨酸羟化酶(oxygen-sensing prolyl hydroxylases,PHDs)羟基化,致使HIF-1α 与肿瘤抑制蛋白(von Hippel–Lindau protein,pVHL)结合。pVHL是E3泛素蛋白的组成成分,HIF-1α 与之结合后能很快被蛋白酶体降解。而在细胞内氧浓度低于6%时,α亚基上的脯氨酸不能被PHDs羟基化,这样HIF-1α亚基就不会降解而持续存在于细胞中。
研究发现,PHD和HIF不仅与缺氧相关,同时也参与了炎症反应过程,也就是说,这两位组成了缺氧和炎症之中的“鹊桥”。
 那么这架鹊桥是如何联系二者的姻缘呢?说到这,就不得不提以下几位“红娘”了:
那么这架鹊桥是如何联系二者的姻缘呢?说到这,就不得不提以下几位“红娘”了:
首先是核转录因子-κB(NF-κB),它是炎症反应的重要参与因子(它与HIF的关系详见原文图2)。在大鼠的炎症性肠病研究中,科学家发现PHDs等可以激活NF-κB,从而增加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的量,同时减少肠道上皮细胞的凋亡。缺氧可以通过增加TLRs的表达放大NF-κB通路,从而提高抗菌物质的产生,刺激吞噬作用,募集白细胞等;反过来,NF-κB的调节因子——IκB激酶复合物也可以在炎症中调节HIF-1α的转录。
第二是自然免疫中的骨髓细胞(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肥大细胞、树突细胞、NK细胞等)(自然免疫、获得性免疫与缺氧的关系详见原文图3)。缺氧情况下,HIF-1α 可以使得这些细胞产生ATP,刺激它们的免疫活性,也可以抑制中性粒细胞的凋亡。
第三是获得性免疫中的T细胞。HIF-1α在辅助T细胞中的表达可以使得更多的Th1细胞表型转变为Th2细胞表型,抑制Th1介导的抗菌作用。HIF也可以刺激调节性T细胞的分化,增加腺苷酸的细胞外水平。
第四是炎症反应中的黏膜上皮细胞。在炎症性肠病和急性肺损伤中,缺氧激活的PHD-HIF通路可以促进黏膜上皮的屏障功能,也可以增加细胞外抗炎信号分子(如腺苷酸)的表达,增强腺苷酸受体通路等等,从而减弱心肌、肾、肝、大肠中存在的上皮细胞炎症反应。
第五是病原体。在炎症反应中,各种病原体可以使得细胞内的HIF变得更加稳定,例如巴尔通体(Bartonella henselae)、金葡菌、HPV8、白色念珠菌等。HIF的稳定性与被感染细胞的耗氧量改变、ATP水平减少等相关。病原体如绿脓杆菌可以“劫持”HIF信号通路,例如抑制腺苷酸的产生,从而破坏上皮细胞的黏膜屏障作用。当然,在A组链球菌等感染中,免疫细胞内的HIF-1α 也可以增强免疫反应,消灭病原体。
癌症:炎症与缺氧的共同“结晶”
 炎症与缺氧都在癌症的发生发展中有所贡献(具体见原文图4)。一方面,炎症细胞可以释放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促进肿瘤血管的异常化。至于缺氧,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刚才提到的肿瘤抑制蛋白(pVHL)。临床上,pVHL相关基因的失活突变会导致Von Hippel–Lindau 病,使得HIF不能够被降解,细胞内HIF浓度增加。同时,患上这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的人又是以好发毛细血管瘤、透明细胞肾癌、嗜铬细胞瘤等为特点的。那么,HIF和癌症有关系吗?答案是肯定的。经过研究发现,这些实体瘤细胞中的HIF-1α 和HIF-2α水平较高,而且升高程度与癌症死亡率密切相关。这其中的隐情与肿瘤血管的形成过程有关。原来,肿瘤如果缺氧,就会激活HIF,而HIF可以促进肿瘤组织中的血管形成,这些血管与正常血管相比,输送氧气的能力增强了,可以使肿瘤更容易生长。
炎症与缺氧都在癌症的发生发展中有所贡献(具体见原文图4)。一方面,炎症细胞可以释放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促进肿瘤血管的异常化。至于缺氧,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刚才提到的肿瘤抑制蛋白(pVHL)。临床上,pVHL相关基因的失活突变会导致Von Hippel–Lindau 病,使得HIF不能够被降解,细胞内HIF浓度增加。同时,患上这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的人又是以好发毛细血管瘤、透明细胞肾癌、嗜铬细胞瘤等为特点的。那么,HIF和癌症有关系吗?答案是肯定的。经过研究发现,这些实体瘤细胞中的HIF-1α 和HIF-2α水平较高,而且升高程度与癌症死亡率密切相关。这其中的隐情与肿瘤血管的形成过程有关。原来,肿瘤如果缺氧,就会激活HIF,而HIF可以促进肿瘤组织中的血管形成,这些血管与正常血管相比,输送氧气的能力增强了,可以使肿瘤更容易生长。
HIF对肿瘤有如此作用,它的抑制剂是否能够减少肿瘤的血管化,增强肿瘤的放疗敏感性呢?实验室的证据证明了这一点。因此,降低HIF表达的物质成为了癌症治疗的新靶点。此外,PHD之中的一种——PHD2在癌症中表达较正常细胞明显增高。缺乏PHD2的杂合鼠可恢复肿瘤的氧供并通过血管内皮常态化抑制肿瘤转移。因此,抗PHD2的药物也许可以使肿瘤血管“改邪归正”,为治疗癌症提供一种新途径。
缺氧和炎症无论在分子、细胞还是临床水平上都息息相关。对于临床上的各种炎症相关性疾病,如急性肺损伤、心肌缺血、炎症性肠病甚至癌症,都可以将缺氧作为治疗的研究靶点。这些缺氧依赖的信号通路也可以用来减少在大手术中缺氧带来的器官衰竭,甚至缓解器官移植后由缺氧导致的移植物炎症反应。看来,这对冤家背后的不解之缘,一定会源源不断地结出炎症和癌症治疗领域的累累硕果。
来源:Hypoxia and Inflammation,Holger K. Eltzschig, M.D., Ph.D., and Peter Carmeliet, M.D., Ph.D.,N Engl J Med 2011; 364:656-665,February 17, 2011